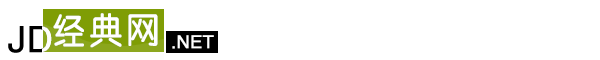第六十二章 幽灵在线阅读「幽灵的幽的第六画是」
乍看去,欧特伊乡间别墅外观上毫无富丽堂皇可言,也不像人们所想像的,这竟是气度不凡,出手大方的基督山伯爵的宅邸。然而,这种朴实的外表却使主人心满意足,因为是他亲自下的命令,外观无需有丝毫的改变。但只要看一下内景,便会使人叹为观止。的确,大门启处,内部景色焕然一新。
这一次,贝尔杜齐奥本人对布局的风格和执行任务的迅速都比以往略高一筹。就像昂坦公爵派人在一夜之间毁掉影响路易十四视线的一条林荫小道一样,贝尔杜齐奥先生则在三天之内,同样将一座光秃秃的庭院,让人用带有巨大整块根土的方法,硬是栽上了漂亮的白杨和埃及无花果树。硕大的树冠浓荫蔽日,遮去了别墅主要门面,房子前以往那杂草丛生的石子小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向前伸去的青翠的草坪。当天上午草坪刚刚整好,宛如一片巨大的绿毯,喷浇的水珠依然闪烁其上。
其它一切安排,也均来自伯爵亲口吩咐。他自己本人就交给贝尔杜齐奥一张样图。栽树的数量和位置、与道路衔接的草坪的形状与间隔,图上都标得一清二楚。
这样一来,房子的布局面目全非。就连贝尔杜齐奥都承认,整个房子像镶嵌在一片绿色之中,连他也认不出来了。
作为管家来说,贝尔杜齐奥既然身在其中,他本来并不反对让花园也变化一番。可是,伯爵坚决禁止触动花园一根毫毛。贝尔杜齐奥只好将会客厅,楼梯和壁炉都堆得花团锦簇,以补偿他效忠主人的余力的发挥。
充分显示服务于人的管家的高度灵巧,和受人服务的主人的渊博学识,还在于这栋房子二十年来空旷寂寥,前一天还是那样阴森凄凉,房中的一切无一不散溢着令人恶心的气味,无处不嗅到年深月久的陈腐气息,而在一天之后竟然变得生机勃勃,面目一新,处处飘溢着主人喜欢的芳香,闪耀着主人喜爱的光线;只要伯爵一到,他的书籍和武器便伸手可取;一抬头,心爱的油画尽收眼底。前厅里,他喜爱抚摩的狗摇头摆尾,他喜欢听的鸟在婉转啼鸣。总而言之,久长昏睡的这栋房子现在醒来了,宛如睡美人的宫殿充满着生机,回荡着歌声,充斥着鲜花,就像我们早已迷恋的那些房子一样,由于不幸而一旦离开,就会使我们本能地留下部分灵魂。
仆人们在这座美丽的庭院里高高兴兴地来往穿梭:有的是膳房师傅,似乎在这栋房子已经久住,从前天刚刚修好的楼梯上轻盈滑下;有的是车库工友,一箱箱编号的设备似乎已经存放半个世纪;马厩里,马夫带着比许多仆人对主人还要尊敬的表情和马儿交谈,马儿发出阵阵嘶鸣作为对主人的回答。
藏书两千册左右的书橱,按两种系列分别沿墙两边排列:橱中各种现代小说琳琅满目,就连前天刚问世的庄严而醒目的红皮烫金本,都已各按其位整齐落架。
和书橱对称的一边是花房,各种奇花异草在日本产的大型养花盆中竞相开放;在这色香奇异的花房中间,摆放着一张弹子球桌,似乎在最多一小时前有人刚玩过,因为弹球还一动不动地停在球桌绒布上。
只有一间房,这位心灵手巧的贝尔杜齐奥未敢动。就是位于二楼左角的那间房,前有宽大楼梯可以走进,后有暗梯可以下楼;仆人们怀着好奇在这间房前来来往往,惟有贝尔杜齐奥心怀恐怖。
下午五点整,伯爵驾到,后边跟着阿里,在欧特伊别墅门前停下。贝尔杜齐奥怀着焦急与不安等待着主人的到达。他期望几声称赞,同时又害怕看到伯爵不满的皱眉。
基督山在庭院下了车,在房中走了一遍,在花园中转了一圈,一言未发,既未发出丝毫称赞的表示,也未显示不快的神色。
只是在走进和那关闭着的房间相对的他的卧室时,他才把手伸向巴西产的香木小桌的抽屉边,这是他到来的第一次特别关注的小家具。
“这只能用来放手套。”他说。
“是的,阁下,”贝尔杜齐奥高兴地回答说,“请打开,您会找到手套的。”他说。
在其他家具中,伯爵找到了他要找的花露水、雪茄烟和小巧玲珑的珍玩品。
“很好!”他说了一句。
于是,贝尔杜齐奥精神焕发地退了出去。伯爵对他周围一切的影响就是如此地大,如此地强,如此地真!
六点整,大门入口处响起马蹄的嘚嘚声。这是我们的北非骑兵上尉跨着梅戴亚来到了。
基督山站在台阶上笑容可掬地等候着。
“我是第一位到达的,我相信准没错!”莫雷尔对东道主高声说道,“我是存心这样做,赶在别人前面先来,好让我有点时间和您单独在一起。朱莉和埃马努埃尔有一大堆事要对您说。啊!您知道,这儿太美了!请告诉我,伯爵,您手下的人会细心地照料我的马吗?”
“请放心,亲爱的马克西米连,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我的马需要用草擦擦身。您知道它跑得多快啊!名副其实的像一阵风!”
“嗯,我相信是真的,一匹价值五千法郎的马哪!”基督山用父亲对儿子的口气说。
“您后悔啦?”莫雷尔爽朗地笑问道。
“我!上帝担保!”伯爵回答说,“不会的,要是马不好我才后悔呢。”
“这匹马好着哩,亲爱的伯爵,法兰西骑马行家夏多·雷诺先生和德布雷先生骑的内务部的阿拉伯马都被我甩掉了,甩得好远呢。我还要告诉您,他们还被丹格拉尔男爵夫人追得够戗,她每小时跑的速度也就是十八公里。”
“那么,他们一直在您后面追您?”基督山问。
“您瞧,他们来啦。”
果然,话音刚落,一辆双轮马车,扬起滚滚尘烟,向敞开着的栅栏门飞奔而来。马车转了一个圆圈,在台阶边沿停下,两名骑士紧随其后。
霎时间,德布雷踏足下地,站在马车门口,向男爵夫人伸过手去。夫人下车时,有一个只有基督山伯爵才能明白而别人难以觉察的举动。
什么都没有逃出伯爵的眼睛,就在这举动中,他看到和那动作一样难以觉察的一张白色纸条,从丹格拉尔夫人手塞到部长秘书的手里。那自如的动作,只有经过惯常的训练才能如此流畅娴熟。
从丹格拉尔夫人身后,走出她丈夫银行家丹格拉尔先生。他脸色苍白,似乎不是从马车里出来的,而是刚刚钻出坟墓来到人间。
丹格拉尔夫人向她周围的人群迅速一瞥,惟有基督山一人心领神会。她接着用探究的目光扫视着庭院、房屋的廊柱和门面,然后,抑制一下轻微的激动,倘若不是面色转白,激动之情定会依稀可辨。她步上台阶,对莫雷尔说道:
“先生,假如您还是我的朋友,我就要问问您,您的马是否想卖掉。”
莫雷尔滑稽地一笑,向基督山转过脸去,像是请求将他从面临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伯爵明白其意。“啊!夫人,您为什么不对我提这个问题呢?”
“和您打交道,先生,"男爵夫人说,“无需提任何要求,因为实在有把握能得到。所以,这就要问向莫雷尔先生了。”
“很遗憾,”伯爵复又说,“我当见证人,莫雷尔先生不可能把他的马让出去,他的荣誉就压在这匹马的去留上了。”
“怎么会呢?”
“他打过赌,要在六个月内驯服梅戴亚。现在您该懂了,夫人,假若他在赌注规定的期限之前脱了手,他不仅失掉了马,而且还会被人说成懦夫。一个骑兵上尉,就是去讨好一个漂亮的女人,依我看虽是人间—件最为神圣的事,但也听不下去别人这样飞短流长呀。
“您瞧,夫人……”莫雷尔一边说一边向伯爵发出感激的微笑。
“但是我觉得,”丹格拉尔插言对妻子说,他那不自然的微笑难以掩盖语气的粗鲁,“像马这类玩意儿您已经够多的了。”
对这样一类进攻置若罔闻而不加以反击,这一点儿也不是丹格拉尔夫人的固有惯例。可是,使年轻人极感惊诧的是,这一次她佯装充耳不闻,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基督山对这种有失惯常和体现屈辱的沉默莞尔一笑,随即指给男爵夫人两只中国造的巨型瓷花瓶,花瓶上绘着做工精美、栩栩如生的大幅海生植物群,惟有大自然才能拥有这种财富,这种活力和这种精灵。
男爵夫人惊奇不已。
“啊!您可以将杜伊勒利宫的栗子树栽到里面了!”她说,“花瓶如此硕大无朋,人们究竟是怎样把它烧出来的呢?”
“噢!夫人,”基督山说,“不应该向我们这些只会做小人像和磨沙花纹玻璃的小工匠提这样的问题。那是另一时代之作,是大地和大海的一种巧夺天工之作。”
“那么,这可能是哪个时代的作品呢?”
“我也不知道,我只听说过中国有某个皇帝派人营造了一座特制的窑炉,让人将十二个像这样的花瓶一批接一批地放进去煅烧。有两个在过猛的火力下破裂了,将其余的十只放进四百八十多米深的海底。大海知道世人对他的要求,向花瓶扔去藤草,缠上珊瑚,镶上贝壳,所有这一切在难以想像的海底经过两百年岁月的磨洗后紧紫粘合在一起,而一场革命赶跑了想作这种试验的皇帝,只留下验证花瓶煅烧和沉入海底的文字记录。两百年后,人们重新找到了这份记录,想把这些花瓶从海底捞上来。派了几个潜水员钻进定做的机器,潜到那投放花瓶的海湾水底去寻找。人们只找到其中的三只,其余的七只被海流驱散和打碎了,我喜欢这些花瓶,我时常想像到里面藏着丑陋,可怕而神秘莫测的水怪,就像只有潜水员们才能亲眼目睹的那些水怪,它们带着狰狞的面孔射出阴沉寒冷的目光;花瓶中还沉睡着数不清的鱼,它们躲藏在里面以逃避敌人的追捕。”
在此期间,丹格拉尔对伯爵稀奇的讲解感到索然寡味,下意识地挑着一棵漂亮桔子树上的花,一朵一朵地扯完后,又走近一棵仙人掌,然而仙人掌不是性格温顺的桔子树,狠狠地刺了他一下。
于是他猛地颤了一下,擦擦眼睛,似乎从睡梦中惊醒。
“先生,”基督山微笑着说,“您是油画爱好者,您是许多珍品的收藏家,鄙人不敢贸然向您推荐我的画。不过,这里有两幅霍贝马的,一幅保罗·皮特的,一幅梅里斯的,两幅杰勒德·道的,二幅拉斐尔的,一辐凡·戴克的,一幅苏巴朗的,两三幅弁利罗的。这些画还值得推荐给您观赏一下。”
“嘿!”德布雷说,“这是一幅霍贝马的画,我认得出。”
“啊!真的!”
“是的,有人曾向博物馆推荐过。”
“我想博物馆没有这幅画吧?”基督山用试探的口气问。
“没有,博物馆拒绝买这幅画。”
“为什么?”夏多·雷诺问。
“您这个人真会摆迷魂阵,还不是政府太穷嘛。”
“啊!抱歉!”夏多·雷诺说,“不过,八年来我天天听到人们这么说,可我还是听不惯。”
“您将来会听惯的。”德布雷说。
“我不相信。”夏多·雷诺回答说.
“巴托洛美奧·卡瓦尔康狄少校和安德烈·卡瓦尔康狄子爵两位先生驾到!”巴蒂斯坦通报说。
内穿一件从服装师那里刚出手的黑缎高领衬衫,下巴留有刚修剪的胡须,上唇蓄着灰色的短髭,目光充满着自信,上装着一件饰有三枚勋章和五枚十字章的少校制服,一句话,称得上一件老资格军入穿的无可挑剔的制服,这就是巴托洛美奥·卡瓦尔康狄少校。我们熟悉的一位慈祥的父亲就这样又在我们眼前露面了。
紧靠他身旁的这一位,全身衣服崭新发亮,笑容可掬地驱身向前,这就是安德烈·卡瓦尔康狄子爵,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彬彬有礼的孝子。
三个年轻人刚才正聚首交谈;这时他们的目光一起从父亲转向儿子,最后又本能地长时间地落在后者身上,并评头品足地议论开来。
“卡瓦尔康狄!”德布雷呼道。
“多高雅的名字!”莫雷尔说,“呵!”
“是的,”夏多·雷诺说,“真不假,这些意大利人真会起名字;可这身衣服穿得挺糟糕。”
“您太挑剔,夏多·雷诺,”德布雷说道,“这身衣服出自高手哩,而且是崭新的。”
“我要责怪的正是这一点。那位先生看样子是头一回穿上好衣服。”
“这两位先生是谁?”丹格拉尔向基督山伯爵问道。
“您不是听到了,叫卡瓦尔康狄。”
“这只告诉我他们的姓,别的毫无所知。”
“啊!不错,您不了解意大利的贵族家谱,所谓卡瓦尔康狄,就是亲王的宗族。”
“家产多吗?”银行家问。
“吓您一跳。”
“他们干什么?”
“他们试图要把家产都吃光,但他们是不可能吃光的。他们前天来看我时,据他们对我说,他们有笔款项要托付给您。甚至是为了您我才邀请他们来的。我将把他们介绍给您。”
“可我觉得他们的法语讲得很地道。”丹格拉尔说。
“那儿子在南方某所大学就读过,我想是在马赛或城郊。您会发现他很热心。”
“对什么很热心?”男爵夫人问。
“对法国女郎,夫人。他决心要在巴黎娶妻子。”
“他想得真美!”丹格拉尔耸着肩膀说。
丹格拉尔夫人瞟了他丈夫一眼,她那表情要是换个场合,定是一场暴风骤雨的前奏,但她又一次压到肚里了。
“今天男爵显得好阴郁,”基督山对丹格拉尔夫人说,“是不是有人想让他当部长,还是偶尔说起的?”
“不,据我所知还没有。我想还是让他搞股票的好,让他输个精光,输了还不知谁搞的鬼。”
“维尔福夫妇驾到!”巴蒂斯坦喊道。
被通报的两个人进来了。维尔福先生尽管强力克制,但激动的面部依然愠色可见。基督山和他握手时感到那只手在颤抖。
“显而易见,惟有女人善于掩饰。”基督山自言自语地说。他暼了一下丹格拉尔夫人,她正在朝检察官微笑呢,然后拥抱他妻子。
和维尔福夫妇见面寒暄之后,伯爵看到贝尔杜齐奥跑进和接待客人的大客厅毗邻的候见室。在此前他一直为杂务忙碌着。
伯爵向他走过去。
“您有什么事,贝尔杜齐奥先生?”他问道。
“大人还没告诉我有多少客人呢。”
“啊!不错。”
“要多少餐具?”
“您自己数吧。”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大人?”
“是的。”
贝尔杜齐奥透过半开半掩的门向客人的房间张望着。
基督山死死地盯着他。
“啊!我的天哪!”贝尔杜齐奥大叫起来。
“怎么啦?”伯爵问道。
“那个女人!……那个女人!”
“哪一个?”
“那个穿白色连衣裙戴许多钻石的……长一头金发的女人!”
“丹格拉尔夫人?”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她。但就是她,先生,是她!”
“她是谁?”
“花园里的那个女人!怀孕的那一个!一边散步一边等的那个女人!……还在等呢!”
贝尔杜齐奥目瞪口呆,满脸苍白,根根头发竖了起来。
“等候谁?”
贝尔杜齐奥没有回答,几乎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贝思》中麦克贝思指着班柯的同样手势指着维尔福。
“噢!……噢!”他终于嘟嚷起来,“您瞧见没有?”
“什么呀?谁?”
“他。”
“这么说,我没有干掉他?”
“他……那不是检察官维尔福先生吗?可能的,我看见了,是他。”
“喂!我想您变成疯子了,我勇敢的贝尔杜齐奥。”伯爵说。
“可他怎么没有死?”
“噢,没有!他没有死,您不是看见他活得好好的。不打中第六和第七根左肋骨之间,这是您的同胞们的习惯,你们不是刺得太高就是太低;而这些法律界的人生命力强得很,就是死不了:要不您告诉我的一切全是假的,那是您想像的一场梦,是您头脑中的一种幻觉。您带着没有消化好的复仇对象入睡了,它就重重地压着您的胃,于是您做了一场噩梦,仅此而已。好了,恢复您的冷静之神吧,那您算算看:维尔福夫妇,加上丹格拉尔夫妇,四位;夏多·雷诺先生、德布雷先生、莫雷尔先生,七位;巴托洛美奥·卡瓦尔康狄少校,八位。”
“八位!”贝尔杜齐奥重复道。
“等一等!等一等!您就这么着急要走,活见鬼!您忘了我的一位客人。稍往左边走一点……瞧……安德烈·卡瓦尔康狄先生,就是身穿黑衣服,在看弁利罗画的圣母像的那位年轻人,他现在转过身子了。”
这一次,就在贝尔杜齐奥开始喊叫的一刹那,基督山的目光就将其扼杀于未然。
“贝内德托?”贝尔杜齐奥小声嘀咕道,“真是天数呀!”
“六点半钟敲响了,贝尔杜齐奥先生,”伯爵严厉地说道,“这是我决定入席的时刻。您知道,我是不喜欢多等的。”
说完,基督山走进客厅。客人们都在等着他,而贝尔杜齐奥则倚着墙,好容易才回到餐厅。
五分钟过去,客厅的两扇大门同时启开。贝尔杜齐奥出现在门口,他像瓦代尔在尚蒂利那样勇敢地使出最后一次努力。
“伯爵先生请用餐。”他说道。
基督山向维尔福夫人伸出手臂。
“维尔福先生,”他说,“请您陪伴丹格拉尔男爵夫人入席。”
维尔福从命,于是客人们一起向餐厅走去。
热门排行
- [网友投稿] 第六十二章 幽灵在线阅读「幽灵的幽的第六画是」
- [网友投稿] 电影,亚当「好看的政治电影」
- [网友投稿] 《竹木狼马》,巫哲「巫哲哪本最好」
- [网友投稿] 关于神道香火类的小说「修神道的小说」
- [网友投稿] 类似妖孽学霸主角天才「硬核学霸」
- [网友投稿] 毛豆煮水喝有什么功效「煮毛豆的营养价值及功效与作用」
- [网友投稿] 双生武魂的优势「双生武魂是什么意思」
- [网友投稿] 我的八一记忆\\「领证纪念日」
- [网友投稿] 《见星》【作者】一只甜兔「见星一只甜兔的小说」
- [网友投稿] 年代文女主是学霸没有金手指「重生七零年代农家女」
经典笑话
- [经典笑话] 定亲
- [经典笑话] 搁 浅
- [经典笑话] 讽刺对客干坐
- [经典笑话] 讽刺对客干坐
- [经典笑话] 嘉兴人
- [经典笑话] 痴人卖羊
- [经典笑话] 文学
- [经典笑话] 兄弟认匾
- [经典笑话] 心在这里
- [经典笑话] 送 匾
编辑推荐
- [网友投稿] 【警察叔叔慢点】最新章节》(独家小说)(全文在线阅读)
- [网友投稿] 贵阳京东白条提现太方便了,实体店N种方式几秒套到手,我已成功取现
- [网友投稿] 美术馆也可以拍性教育短片嘛「美术馆摆拍」
- [网友投稿] 最优美的英文句子
- [网友投稿] 最触动心弦的句子
- [网友投稿] 天津科技大学2021美术类招生简章「成都文理学院招生简章」
- [网友投稿] 国内竞技钢管舞发起人「钢管舞百科」
- [网友投稿] 爱是激情后的沉淀,是思念的累积
- [网友投稿] 关于欢太商城欢太分期额度怎么取现可以秒到吗?有什么流程等问题解析!
- [网友投稿] 《乡村解药》苏颖儿 张大树(完整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
- [网友投稿] 陕北快板说书「陕西快板大实话」
- [网友投稿] 重生之女土匪(重生之女土匪完整版txt下载)
- [网友投稿] 诚信花呗信用购套取现金商家,24小时淘宝店铺套花呗秒到2022已更新
- [网友投稿] 思念心上人英文句子
- [网友投稿] 唯美伤感的句子-情感的折磨,无心则无息